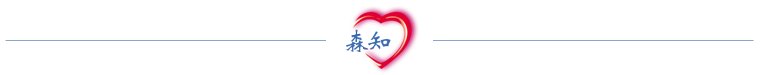进食障碍:我对自己过去的多年暴食充满感激
浏览量:5727 发表时间:2017-04-07
假如你对“进食障碍”这个词有一点了解,你也许和曾经的我一样,认为“对瘦的执念”是这类疾病的症结所在。我一直抱持着这个观点,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个进食障碍相关的公众号上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我对自己过去的多年暴食充满感激。尽管暴食给了我很多问题,但它远好过在少女时期怀孕生子,远好过沾染上海洛因,远好过自杀。在我最糟糕的那些年里,食物给了我保护。只是后来我渐渐学会放下恐惧,我已经不再需要它的保护了。”
它促使我意识到“进食障碍”或许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对瘦的执念”并非不重要,但在这个执念的背后或许还有更多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
今天我们采访了这个公众号的创始人何一,她曾经挣扎于神经性贪食症(见注)中7年之久,而后靠着不断努力康复到正常状态。她建立的公众号帮助到了许多和她一样的患者,同时也因为这段经历,她决定辞职赴美留学,以期未来以更专业的身份投身到进食障碍的防治事业中。希望她的经历能为处于相似困境中的人提供一些参考。
注:根据DSM-5的分类,进食障碍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暴食症及其它特定的进食障碍。
Q1:在你记忆里,你第一次出现症状是什么时候呢?
A:其实,我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没有进食障碍的症状了,“没有症状”指的是我现在没有强迫性节食、强迫性暴食,没有像催吐、使用泻药这样的行为,也不再一天到晚想着食物。
“第一次出现症状”是很难定义的。一方面,进食障碍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不健康行为的频率和程度是逐渐加大、直至达到临床“显著”级别的。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谈恋爱一样,你说不出你哪个点爱上了对方,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我已经爱上了。另一方面,进食障碍的症状有很多种,我已经不记得具体哪一种症状从什么时候开始。
但在17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采取一些极端行为来控制体重:我会暴食,还有使用泻药、过度运动这样的“清除性行为”,想要清楚吃到体内的食物。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一次催吐,那是18岁那年的除夕,虽然我平常把自己控制得特别紧,但身边所有亲友都劝我多吃,然后我也就一直吃,撑得自己非常恶心和难受,到自己已经觉得忍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偷偷跑去厕所第一次催吐。
那时家里非常热闹,大家看春晚的看春晚、打麻将的打麻将,没有人注意到我中途溜走了两次又溜回来,一切就都被虚掩了起来。
Q2:当时,你对催吐的危害有所了解吗?
A:其实还没有意识到催吐行为的危险性,只是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很棒的方法,又可以让我吃很多好吃的,还不会吸收热量”。等我回到学校,也不断地去重复那个行为,一开始还是主动选择去催吐,但后面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强迫性行为,不是我吃了很多,而是只吃了一点点,也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催吐。那种冲动特别强烈,让我有一种“被淹没感”。
后来我才知道催吐对身体有很多危害,比如说会影响身体的电解质平衡,可能导致心律不齐,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心脏骤停。美国体操运动员CathyRigby退役后公开了自己的催吐行为,她曾两次因电解质失衡导致的心脏问题住院。另外,催吐会导致胃酸逆流,侵袭食管、喉咙,可能永久性地伤害牙齿。比如我现在牙齿就很差,这也是进食障碍的一个不可逆的伤害。
但当时,想去清除食物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毒瘾发作一样。在我的了解里,包括我自己、和我交流的其它患者、还有文献里读到的一些案例,很多有进食障碍的人在认知层面上并不是不知道暴食和催吐不好,但就是没有办法去控制。
Q3:回到学校之后,你催吐的行为重复甚至恶化了,那当时周围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A:没有。当时我一直非常小心地掩藏自己的行为,因为感到很羞耻,觉得它是病态的。那个时候住宿舍,去厕所怕被听见催吐的声音,我就会放抽水马桶的声音来掩盖。但其实我不止一次听到过其他隔间有人发出一样的声音,那个声音我太熟悉了,我知道她一定是在催吐。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另一方面我又没有勇气去见一下那个女生是谁。
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催吐的应该不止一个人,当时身边群体的进食障碍发病率应该是相当高的。我本科和硕士念的都是女生偏多的学校,身边人的形体焦虑非常严重,还有同学会吃很夸张的减肥药,甚至出现幻觉。
Q4:那你后来是怎么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进食障碍”呢?
A:其实我一直知道“进食障碍”这个词,也隐隐地有所怀疑,但就是很害怕面对,也不愿意去了解更多。直到23岁那年的夏天,我在一个月内两次在自己的催吐物里看到有血。
我特别惶恐,很怕血是从胃里或食道里来的,怕自己会得食道癌、胃癌。看到血,真的触发了我的求生本能,就觉得我真的得了解一下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件事促使我去搜索这个疾病,那时我才肯承认,我已经处于符合DSM对贪食症的诊断标准的状态很多年了。
Q5:你知道自己可能是贪食症患者之后,有采取什么行动吗?
A:当时我的病耻感实在是太强烈了,觉得自己是一个怪物,没脸跟任何人说,所以只敢从网上买一堆自助的书,自己执行CBT(认知行为疗法)和ACT(接纳与承诺疗法)的疗程。一段时间后病情稍微稳定了一点,我的自信心也增强了一些,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像一个怪物了,才敢去北医六院看病。
再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治疗,慢慢康复后,我才敢跟身边的好朋友承认其实我有这个疾病。但当时我还挺幸运的,身边的好朋友都给了我温暖和支持。我到更晚一些才告诉爸妈。
但是现在回头看,如果那时我的自我接纳程度能再高一点,能有勇气再早一点跟身边的同理心比较强、能够理解我的人说的话,康复的过程可能会走得更容易一点。我个人觉得,进食障碍很难纯粹靠一个人的力量来康复,我们还是需要从健康的社会关系里去得到支持。
Q6:和朋友第一次坦陈病情的情形是怎样的?当时是怎样一种动力支持着你?
A:可能就是出于一种希望坦诚做自己的动力吧。因为我觉得进食障碍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是我那么好的朋友,我希望能让他们看见更完整的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的那一部分遮掩起来。
第一次是发QQ说的,当时我还不敢挑我身边的人,选了一个在外地的朋友,发消息告诉他我有贪食症。即使他离我很远,我说完后还是超级忐忑,像要被审判一样,心跳得超级快。我记得他当时回复我的第一句话是,“嗯,你说的就是戴安娜王妃得的那个病吗?”那一瞬间我非常感动。因为当时我有一种误解,就是所有人知道我有进食障碍,都会骂我是变态、会离开我。但他完全没有看不起我的语气,而是用一种很平常的语气在跟我交流。那个时候,我能从她身上感觉到一种没有评判性的接纳。
我后来慢慢接触到一些进食障碍孩子的家长,他们其实很关爱自己的小孩,但是在表达方式上有时会出现评判性的语气,就会容易让孩子们反感。比如有的家长会说:“你努力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好转?”这对康复进程的伤害其实挺大的。
Q7:你也有提到,后来和父母沟通过自己的病情,当时情况如何?
A:我跟父母就这个问题沟通过三次,都是在症状稳定、也就是没有明显的行为症状之后。
第一次是在视频聊天里,狂哭着说了一堆。不久之后就和父母当面聊了第二次。当时我对自己的疾病的理解比较有限,会忍不住去追溯青少年时期我妈妈一直嫌我很胖,送我去减肥的经历。比如,14岁还在生长发育时她送我去用饥饿疗法减肥,但我回头看14岁的照片,虽然不瘦,但是远远没到重度肥胖、需要干预的程度。17岁时我妈还给我买了减肥药西布曲明。在当时的我看来,吃药是减肥的捷径,就把药吃了。过了几年,西布曲明被下架,因为西方研究发现服用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一系列事情都让我觉得我妈妈多多少少要为我的进食障碍负责任。所以在第二次沟通中,尽管我试图不去指责她,但是话中还是有指责的意味。这也激起了我妈的防御态度,我记得她当时说了一句话:“照你这么说,妈妈爱你二十多年都白费了是吧?”第二次也就不欢而散了。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我不仅一直在用完美主义的标准对待自己,也在用它对待自己的父母。我一直在期待爸妈是完美的人,但是事实上他们和我一样也有缺陷。所以我不仅需要接纳自己,也需要去接纳爸妈的不完美,还有整个生活的不完美。
所以后来,我又和爸妈长谈了第三次,是在去年出国之前给他们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为第二次沟通道歉,说自己当时不太懂事,急于找一个替罪羊来为我的进食障碍负责,所以说了一些让妈妈伤心的话。当时我妈妈的反应让我很意外,她说:妈妈当时也有不对,妈妈回忆了养育你的过程,觉得也有能做得更好的或者不同的地方,妈妈要向你道歉。当时我听了也超级感动。
跟爸妈的这三次沟通,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一个小家庭,修复式地往前走的一个过程。
Q8:对于“自己为什么会得进食障碍”,你的想法是有变化的吗?
A:对,我对进食障碍的成因在不同阶段的理解特别不一样。
在我刚刚意识到自己有问题时,我的进食障碍症状还处在活跃期,我那时觉得得病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是因为我自己作、瞎减肥、爱慕虚荣、觉得瘦就代表成功和幸福。后来我发现,其实这种想法是进食障碍患者非常典型的想法。
后来我病情慢慢稳定后,我越来越多地看到,其实进食障碍的成因里有我控制不了的因素。比如说我奶奶有精神疾病史,我的基因很可能就增加了患病风险。另一个是宏观的文化环境,我在一个崇拜“瘦”的男权社会里出生和长大,尽管很多被认为是“美”的标杆的东西本身是不切实际的、有害健康的,但我把这些标准认为是理所当然,意识不到这是危险的。
这个社会又会给女性很多压迫性的条条框框,比如女性应该专注家庭、不能对事业有太多追求,当我不愿意去顺应这些传统价值观的时候,就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它们都会变成焦虑和抑郁的来源。
而当我感到痛苦的时候,整个环境又会给我一种暗示:“女人的不行都是因为你胖、你丑,瘦的、漂亮的女孩才不会有痛苦,变瘦就可以解决你的痛苦。”这种想法成为了我解释各种问题的思维定式,比如我会把喜欢的男生不喜欢我归因于我太胖了,而忽略了男女同时看对眼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会把参加工作之后没有很快得到提拔也归结于我外形不好,而不去思考其它的原因。
然后暴食、催吐这些行为就在无意识下成为帮助我逃避生活中痛苦的工具,因为要面对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实在是太难了,相比之下,“变瘦”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可操作的任务,所以把精力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就可以回避掉很多不想面对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疾病的理解就是:基因给我上了膛,然后环境扣了扳机。
Q9:你说到暴食、催吐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你逃避生活中的难题和痛苦,那你是如何从它带给你的这种“保护”中走出来呢?
A:食物给我的安慰、对瘦的偏执,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支撑我运作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即便我知道这一套价值观有问题,但我需要这个“拐杖”来支撑我生活下去,如果马上要我放下执念,我整个人都会散架。
所以我需要慢慢地去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然后再慢慢地放开之前的那一套拐杖,逐渐接纳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个过程很难,因为尽管你知道新的东西很好,但你依然会对陌生的事物有天然的不信任感。康复后期其实我很怕感觉到快乐,因为我觉得幸福马上会消失,我一定会回到痛苦中;处在那种每天都很焦虑的生活状态虽然很糟,但是我很熟悉,我反而会更安心。所以要转变那个价值观一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很多旧的信念需要被打破。
甚至新的信念体系建立后,不代表旧的想法就不会再回来了。比如,我现在有时候在朋友聚会的场合多吃了一点,那种催吐的想法还是会回来,只是现在我不会再付诸行动。
但现在的我,不会觉得这些念头的出现会多可怕、多令人吃惊,因为我知道想法和情绪的内容本身不是问题,怎么应对它们才更重要,而我现在可以有能力应对这些想法。
从进食障碍中康复真的挺难的,尤其是生理上的成瘾感还没有明显退下去的时候。刚开始决定要康复时,我会很害怕吃饭,因为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吃饭了,很怕自己一吃就又吃过头。对于酒瘾患者或者毒瘾患者来说,生活中没有酒或者没有毒品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但食物却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不可能不吃东西,所以我必须要去面对它,这意味着我需要跟食物重建一种新的关系。
暴食-催吐的循环是不容易打破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康复更重要的是要在一开始意识到: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慢慢的进步,而不是完美。不可能我今天下决心,一两个月内就能够有奇迹般的恢复。一开始,症状频率慢慢降低就是很好的事情,比如你原来一个星期催吐五次,下个月你变成一个星期催吐三次,虽然看起来你每次催吐的时候还是压力很大,觉得我怎么下定决心要康复了还催吐,但其实从每周五次到三次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这不代表你又重回旧轨了,而代表着你有进步,你还需要继续往前走。
当然康复的动力也不是一直都有的,就像两个人相爱并不是一直相爱,爱的感觉是间歇性的,康复的动力也是这样。生活中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可能你恢复得好好的,某个突发事件又把你打退到康复能量比较低的状态。但我不会觉得病情恶化是能力不足或意志力不坚定的表现,因为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都只能尽己所能。你常常会觉得很没有信心,尤其是每一次复发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我是不是永远都好不了了。但就是那种破坏性的情绪过去之后,你还是要找出那个动力,要继续朝前走。
Q10: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用过什么具体的工具或者方法吗?
A:每个人的康复历程不太一样,所以要强调一下,我用的方法不一定对其他人适用。我个人在不同阶段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比如一开始用的是认知行为取向的方法,我会给自己做饮食日记,记录我每天吃了多少,当时吃的场景是什么,吃前吃后有什么想法和感受,那天有没有暴食和催吐,如果有的话,我事前事后的想法是什么。饮食日记是促使我诚实面对自己的方法,同时它也记录下来我病情的基本情况。在它的帮助下,我发现了一些自己的病态模式,比如我每一次去完超市都会暴食。之后我去超市,路过贩卖我之前经常暴食的食物的区域的时候,我就会提前做一些其他的预防措施,来让自己不去把这个风险因素变成真的暴食行为。
另外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康复动力并不是一直都那么稳固,所以我会在自己很有力量的时候写下一段鼓励的话,存在手机上,然后在暴食、催吐的冲动突然来袭的时候,拿出来给自己念几遍,后来我在公众号上也发起过这个活动,叫“给自己的鸡毛信”。
行为层面逐步正常之后,我就花了更多精力和时间处理心理层面的问题。到现在,因为再也没有以前的行为症状,所以我也没有再记饮食日记了,但我还是会进行一些固定的康复活动,因为我需要维系自己的康复状态。
比如,周末的时候一般我会做冥想练习。我还会不时地给自己写一个感恩清单,一开始真的写不出来,觉得生活中有什么好感恩的,但后来慢慢发现这个对自己挺治愈的,比如说感恩我爸妈很支持我,感恩现在有片瓦遮头,或者感恩今天天气很好。写这个也是思维练习,培养自己发现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东西的能力。我最近压力有点大,找实习不是很顺利,写清单的时候我发现经常会把难题写进去——感恩生活中有这个难题,让我来面对,解决完这个难题之后可能自己就会变得更有智慧、有勇气一点。
我有时会感觉,康复稳定后我的生活好像变得更糟糕了,当然并不是真的更糟糕,而是说明我能够直面生活中其它的问题而不再去逃避了。我有一个朋友说,以前进食障碍就好像一团浓雾,挡在她和她自己真实的生活中间,现在这团浓雾消失了,她可以深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当然生活有它本来的样子,它会有很多让我们很感动的东西,也会有让我们觉得很糟糕的时候。但康复的价值就在于:生活很惨的时候,你是很清醒地去经历的。
Q11:我记得你在文章里写过“我认为自己在康复,但不认为自己会痊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A:我自己的理解是,进食障碍和很多其它的精神疾病一样,本身就是不能被治愈的,但是它们可以被控制住。行为症状消失了并不代表你康复了,内心的成长是没有尽头的。比如我自己,我没办法改变自己的基因,我的基因风险性还在,我会始终有那种强迫性的把事情做得很极端的倾向,我也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危机。所以,我觉得康复是一个终生的过程,我需要努力去维系它,来保证自己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不再用过去的暴食、催吐这样不健康的方法来应对,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反而感到很安心。当然,要强调的是:不能痊愈不代表疾病不能被控制住,也不代表患者不能过很充实很精彩的生活。
Q12:那你会不会担心自己被贴上“贪食症患者”的标签,对这个标签你怎么看?
A:我现在是不害怕的,因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我的一个标签。甚至我自己常常主动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比如我留学之后在班上自我介绍时,就直接介绍我念现在这个专业是因为自己有贪食症的经历。
过去这个标签曾经带给我很大的羞耻感,比如一开始,要在搜索框里打出“进食障碍”这几个字的时候我都打不出来,写日记我也会用其它符号去代替,因为我没有办法面对。但现在这是一个让我感觉很有力量的词,如果不是贪食症,我不会看到我生活中其它更深层的问题,不会真的开始走上康复的道路,也不会因此去美国读临床社工专业。我希望以后可以做进食障碍的预防和治疗工作,所以希望通过学习让自己在这方面更专业一些。
Q13:据你了解,现在国内针对进食障碍防治的资源是怎样的情况呢?
A:我了解比较有限,也仅仅是分享信息,而并非是给这些组织的服务背书。
大陆这边,据我所知只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大连市七院,有进食障碍的诊疗专科。其它有些医院虽然没有进食障碍的专科,但它们可能有精神卫生科或者其他治疗力量,也能为康复提供一些支持和资源。
另外还有专门服务进食障碍者的康复团体——嗜食者匿名会,这是个非营利性组织,目前在北京和上海有线下的分会。
预防方面,国内基本没有资源。我们公众号有时候写一些倡导类的文章,其实是希望能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
营养治疗也是进食障碍治疗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据我所知,六院的进食障碍团队一直想招专门的营养师,但国内懂进食障碍的营养师很少,所以至少在去年以前还是由医师靠自己的医学和营养学知识来指导营养治疗。
Q14:很感谢你的分享,最后如果邀请你对处于进食障碍相关困扰中的人说一段话,你会想说些什么呢?
A: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吃饭,饮食适度,能够对社会环境、对瘦的标准和节食文化有一个更加理性、批判的态度,能去看到其实这个世界是很多元的,然后更好地去接纳自己、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