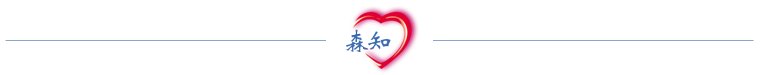对情感婚姻的不满
浏览量:5345 发表时间:2016-01-24
这间酒楼在这个尴尬的地方存在了起码有十年,刚开张时搞出过溜冰鞋送菜的花样吸引顾客,后来靠做外地团队游客的生意,尽管一直处于倒闭的边缘,却一直摇摇欲坠地维持着。现在干脆在门口支了不锈钢的大锅,卖起小龙虾。写着新郎和新娘名字的招牌就摆在锅子的旁边,一张粉红色的纸,上面印着红色的楷体 ,箭头盲目地指向昏暗的大厅。
才华算什么呢?谁稀罕!
选择这种地方结婚,要不就是玩笑,要不就是对情感婚姻的不满。
但是新郎和新娘确实认真站在那儿,背后贴着几张结婚照。照片也像是因为时间来不及而匆促拍的,两个人的合影被处理在了不同的背景板上。最大的那张,他们站在沙滩旁边。
新郎是山丘的出版商,和山丘差不多年纪。瘦,头发披肩。保留了一种八十年代诗人的气质。新娘看不出年纪,但是肯定比阳阳大不了多少,一副过时的长相。可能是眉毛的问题,眉毛描得太细了,直直戳向太阳穴,看起来有股煞气,并不太高兴似的。
山丘怂恿阳阳一起过去和他们合影,她拒绝了。站在一旁等他时,她在大厅里认出了老五,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诗人,半衰期里有不少人把他当成偶像。模仿他的诗歌,跟随他的态度立场,把他二十年前一张著名的黑白照片当作头像。他现在衰老得可怕,但是放浪形骸的姿态在人群中依然很容易被辨别。头发掉了大概一半,剩下的一半染成了金黄色。肥胖,毫无疑问。他们这个年纪的诗人或者作家几乎都难逃身材走形的厄运。他的牙齿有问题,一定是掉了几颗,他不说话的时候都在吮吸嘴唇,这让他的脸看起来像是塌陷了一样。
他身边的女孩比他高半个头,一副运动员的身材。大概才二十岁,圆盘脸,涂着厚厚的粉,脑袋后面垂着一条结实的马尾辫。她始终紧紧挽住老五的胳膊,手指神经质似的来回摩挲,小鹿般的眼睛紧张地瞪着周围每个人。她穿得过分隆重。绛红色的连衣裙,拦腰绑着一根褐色的编织皮带。大厅里还没开空调,她额头的刘海汗津津地耷拉着,像是从八十年代的挂历上走下来的。
山丘带着阳阳和他们打了招呼,老五嘻嘻哈哈地打量了她一番,要求山丘介绍这位未曾谋面的美女。
“山丘老师,我刚看过你的小说,你长得和照片上一模一样。”老五的女友说,语气里带着拘谨的讨好。
“山丘的小说有什么好看的,要看也得看看福大师、海大师什么的啊。”
于是女孩掩着嘴笑起来,五官局促地挤在一起。阳阳隔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老五是在说福克纳和海明威。她不知怎么的,并不想参与他们的对话,把头转向了其他地方。
“也不知道阿亮是怎么想的,就算是第二次结婚也不能搞得这么简陋。”
“应该都是女方亲戚操办的。他俩本来就打算领个证。”
“新娘是干吗的,也没听阿亮提起过,怎么突然就结婚了。”
“好像是个老师,在外地什么地方教书的。怀孕三个多月了。”老五挤挤眼睛,酒席还没开始呢,他就已经喝完了两瓶啤酒。
“哪里人啊?”
“不知道,没听说过的小地方。她家里人的两辆大巴刚刚还堵在高速上。”
“上回喝阿亮的喜酒是什么时候,得有个十几年了。”
“何止,快二十年了。我大学刚毕业,你还在念大学。那场酒多气派。”
“是啊。在珠江饭店吧?那饭店还在?”
“早拆了。”
“小紫不知道怎么样。”
“前几年不是跟那谁结婚了吗,她真旺夫,嫁了个画家以后,那家伙的画就嗖嗖往国外卖。再看看阿亮现在落魄得。”
“落魄也谈不上,不过当年做红那几个女作家时,确实威风过一阵。”
“往事。”老五挥挥手。
阳阳到门外抽了根烟,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刚刚停下两辆大巴,新娘家的亲戚从上面陆陆续续下来,不知道坐了几个小时,站在那儿伸胳膊蹬腿,看起来都疲惫万分。一个哭泣着的小孩蹲在地下突然尿了起来。旁人看来,还以为是某个乡下来的旅行团在这儿歇脚。新娘提着婚纱走了出去,所有人都在高声讲话,外面吵成一团。
新郎只请了他们这一桌朋友,桌子被勉为其难地安置在了角落里,不知道是怕他们被其他人打扰,还是怕其他人打扰了他们。
阳阳扫了一眼宾客名单。有一位隐退了多年的作家,阳阳高中时读过他的小说,他总共就出过两本书,之后据说一直在郊县的师范学校里教书,半衰期的论坛里一度常常谈论起他。阳阳记得他写一个摇滚歌手,写他在台上像条狗一样跳来跳去。除此之外,阳阳对他的小说全无印象,倒是他突然隐退的行为偶尔还是会被人提起。
其余还有几位出版商,画家,报社文化记者,以及他们带来的家人,等等。
很难把这些名字和在座的人对起来。除了老五,其他人都更加没有特征。她猜测正对着她坐着的那个男人或许便是那位作家,剃着很短的头发,运动员身材,脸上没有太多神情,喝着面前的茶,茫然地环顾四周。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看起来都差不多,没有人像老五这样走形得厉害,却也没有第二个山丘。
大部分人并没有把注意力特别放在阳阳身上,他们多半已经对出现在山丘身边的女孩习以为常,甚至都懒得多问两句。只有一个美国男人郑重其事地和阳阳握了握手,他的眼睛湿润,灰白交杂的头发盖过耳朵,难得的彬彬有礼,自我介绍说他是个翻译,叫麦克,中文流利得很。他坐下以后还为阳阳倒了一杯酒。这稍微令她感觉自在了些。
他们的谈话出乎意料地无趣,大部分时间是在聊过去的朋友。大部分都发财了,小部分依然贫穷。大部分从良了,小部分依然放浪。哪怕是那些乌糟糟的诗人,也都莫名其妙地赶上了时代的浊流,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真奇怪啊。他们感慨,既感慨别人,也感慨自己,仿佛什么都没做,无需任何努力,甚至不需要挪窝。运气好的人总会被浊流带走,而运气不好的人,只要死皮赖脸活着,便总有轮到他们的那一天。
这时灯光暗了下来,响起音乐。新娘拖着长长的裙裾入场,新郎规矩地站在走道的尽头等待,双方都不太熟练。和所有其他婚礼一样,一旦四周的吵闹声停止了,气氛便自然有些伤感。但是灯光很快就又亮了起来,几乎有些刺眼,有那么一会儿,在座的各位脸上都还来不及收起感慨或者叹息的神情。
只有老五轻声嘀咕:“你们不觉得吗,女人经历了这种感人的场合以后都变得非常渴望婚姻情感,男人就变得更加恐慌。没错吧。”阳阳用余光扫到他的女友在他大腿上掐了一把。
旁边的几桌亲戚都已经酒过三巡,有几个过早喝高了的亲戚腆着肚子四处敬酒,残存的感伤立刻被骤然升温的喧哗扫荡一空。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桌竟然有个美国人,于是都围拢过来打招呼。麦克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转眼就被灌下三杯白酒,摇晃着几乎站不起来。他个子特别高,接近两米。那些舅舅伯伯们就这样笑眯眯地围着他,不停地问他。你有女朋友吗?美国人结婚的时候是不是都要去教堂?
阳阳有点同情他,但是他们桌的其他人没有帮他解围,他便一个一个问题认真地回答。在得知他还是单身以后,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年轻女人被推搡到了跟前,她染着褐色的头发,大家哄闹着要求她和麦克喝交杯酒。因为被推搡,所以她几乎就要扑进麦克怀里了。
婚礼进行到了高潮,孩子们在大厅里尖叫着四处奔跑,服务员们穿梭着端上来一盆盆热菜,而他们桌上的人在把老朋友草草地谈论了一番之后,反而陷入了沉默。
过一会儿,有人提起说,怎么小河不来。
听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通之后,阳阳大致知道,这个叫小河的女人是个作家,和他们差不多年纪,阿亮当年出版过她的书。
“你看过她的书吧。”山丘问阳阳。
“谁?”她对这个平淡无奇的名字毫无印象。
“她之前用的是笔名。”他说出一个熟悉的名字。
“哦。哦。”
整篇小说没有任何身体描写,偶尔有动作,几乎全部是对话。却是阳阳读到过最好的描写性的小说。那么有力,那么针锋相对,那么痛苦。
那是十年前,那会儿她大概就是阳阳现在的年纪,一旦想到这儿,阳阳几乎就要嫉妒起来。当时,其他同龄的作家还没有开始写性,或许他们也在写,但是和她相比,他们写得都太软弱,不值一提。没有人像她那么写。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女人,所有女人都太把性当回事了,唧唧歪歪,没完没了。她却设法保持住了理智。
“她当时要是不离婚讲不定现在也不会变成这样。”
“年轻时谁知道啊,个个都觉得自己能征服全世界,我们不也是吗,对谁都不服气。”
“但是老赵对她是真爱,看得出来,对她是全身心的投入,写了多少评论文章啊。没了老赵,她还真是不行。”
“她那会儿多漂亮,真是漂亮,第一次看到她,在老赵家里,真是连话都不好意思和她说。你们还记得吗,她头发披到屁股,像绸缎似的,红裙子里连胸罩都不戴。”
“唉。”
“啧啧。”
“阿亮肯定是请她了,但还是不来的好,她现在就是个惹祸精,说话没半句真的。”
“是啊,有回半夜里还给我发消息呢。老五,就是前几年你在香港诗歌朗诵会那次,问我要不要一起去香港。我心想我跟老五是什么关系,还要你从中间传话呢。那段时间她和不少男人好过。”
“算了吧,她可看不上你。我去北京见她的时候,她和大导演好着呢。”
“哈哈哈哈。”
“她真应该来的,好多年没见了。”
“还是别折磨她。她有抑郁症,让她自己待着吧。”
“应该写写她的,怎么就没人写写她呢。写写才华是怎么把一个女人给毁了的。”
“有什么值得写的,不值得。”
“是啊。没有一个女作家值得写,男作家还能写写中年危机,她们连中年危机都没有。看看她们开会的时候都讨论些什么就知道了,见面就谈打牌。”
“唉。唉。”
“你们说,才华是什么啊,这儿谁没有。真是不稀罕。”
隐退的作家突然开口,然后举起酒杯来,大家默默喝了一杯。
麦克喝完这一杯,就歪过头去吐在了旁边的花盆里,随后栽倒在桌子上再也没出过声。所有人都喝多了,变得更加沉默,只专注于自己眼前的酒。只有老五的女朋友,酒精完全没有打垮她。这会儿她把头发散开了,在习惯了她的俗艳之后,便会觉察到她迷人的地方。其他人都放下了筷子,只有她还饿着,酒精也让她不再那么局促。她站起来夹菜吃,腮帮子塞得鼓鼓的,发出生机勃勃的咀嚼声。她近乎野蛮粗鲁的年轻把其他人都衬得死气沉沉。
他们喝掉四瓶白酒,四瓶红酒,六瓶黄酒、若干啤酒。其他人怂恿老五再去问服务员要一些啤酒。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迟疑着,突然就收拾起东西,挥挥手说要走了。
“怎么急着要走,酒还没有喝够。”
“等会儿,等会儿。你总得等到阿亮来敬酒。”
他们纷纷起身想要拖住他,他的女友也瞪圆了眼睛,嘴巴依然没有停止咀嚼。
“没法再这样等下去,结婚真是没意思透了。”老五摆摆手,固执地披上外套。
等到老五和他的女友离开以后,酒桌上顿时更安静了。
“你们说,为什么我现在对生活完全提不起兴趣呢?”隐居的作家突然说,他的目光茫然地扫过在座所有人,又落回他的酒杯。他重新打开了一瓶啤酒,身体却没法再动弹了,便停在那儿,看着泡沫迅速漫了出来。
“对文学也是。”他说完,垂下了头。
阳阳转过头去看了看山丘,他也正看着她。整顿饭他们几乎没有怎么说话,山丘大部分时候也是沉默着的,他现在看着她,慢慢地从嘴角扬起微笑,又有些羞怯似的把目光移回酒杯,然后又移了回来,不好意思地摸摸头,叹了口气。
而她呢。她喝多了,最后那杯啤酒——或许里面还混着些白酒——把她带入了身体和情绪的泥沼。她知道很快就会再次感受到没有尽头的痛苦,但是此刻,她放松而愉快。尽管她当时完全没有把日后的痛苦放在心上,却还是下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犯傻,绝不能把这当成是爱情。